
圖文/鏡週刊
青春期的他去舅媽家作客,舅媽為他準備了一床雪白簇新的被褥床單,夜裡夢遺,覺得羞恥,自此對性懷著巨大恐懼,「你不手淫嗎?」「以前不手淫,因為包莖過長,打手槍很痛,但現在開始了,因為怕攝護腺肥大。」他期待夏天,捷運上偶然見著了穿背心的男孩,看見了腋毛、若隱若現的乳頭,震顫如射精,彷彿活在一部春宮電影裡。「對愛情可還有憧憬?」「我迷戀容貌很美,腰很細的男孩,我總幻想著這樣一個男孩他不能忍受我,突然拿刀把我殺死。然後我生命中最後看到的就是那片美好。」
滿屋雜物現實脫節
男色美好,但若要他在陰莖跟鸚鵡必須選一個?「當然是鸚鵡啊。」他講得斬釘截鐵,口氣不以為然,彷彿我問了一個笨問題似的。他生活簡樸,早年買1塊資生堂香皂,介於紫色桃紅之間,半透明多美麗,他只在特定的時間拿出來洗臉,譬如每年的8月21日,因為是鸚鵡到他們家的日子,1979年8月21日。在這個世界最深刻的關係,除了母親,就是鸚鵡和鵪鶉。小鳥會跟他接吻、撒嬌,他愛他的小鳥們,像愛情那種愛,2006六年,他改了名字,「我家的鸚鵡和鵪鶉會讓我忘記憂愁,牠們給我安慰,給我鼓勵,我把牠們的貢獻也放在名字上,這樣我們就合為一體。」我說那簡直是冠夫姓,他抗議:「我本來是叫做鸚鵡鵪鶉李幼新,但戶政事務所說姓不能改。」

姓不能改,但丟了父親給的名字,無異於哪吒割肉削骨,還諸父母。父親李維新生於清宣統3年,2005年過世,享壽95歲,母親嚴清華今年100歲了,依然健在。父母老來得子,年紀差距如祖孫,但父子一輩子都在吵架,什麼難聽的話都罵過。父親是1949年跟蔣介石來台的職業軍官,他從小在板橋眷村長大,「我一直想解放我媽媽,希望她離婚,會讀書寫字,那時候外省女人可吃香了…」
母親是江蘇鄉間大戶人家,以為嫁到上海有好日子過,誰知做牛做馬,得外出工作,除奶奶和父親,還要養活伯伯、伯母一大家子。他對女性主義的擁戴,完全來自對母親地位的不平之鳴。成年之後,父母逼著他結婚,他說就算你們抓著我的陰莖放到女生的陰道我也沒辦法,我喜歡的是男孩子。結果母親聽完不生氣,怒視著父親說:「你看,就是你早年在上海尋花問柳,玷汙了許多良家婦女,遭報應,斷了子嗣吧。」

父親晚年去住養老院,父子遠著距離,感情反倒好了。母子與一群鳥相依為命,日子倒也愉快,他說有時候一早去外地演講,要母親叫他,「那時候去高雄搭台鐵四小時,早上6、7點起床,我媽怕太早叫我,我會睡眠不足,太晚叫我,又怕我會趕不上火車,她會在黑暗中睜大眼睛,嚇得一個晚上不敢睡。」2008年5月,母親在鸚鵡與鵪鶉的房間跌倒,一群鳥看著她,訝異不出聲,媽媽知道他當天要開會,忍著痛不去叫他,辛苦掙扎,獨自爬了很久很久。老人怕跌,此後遷居安養院,他總是帶著鸚鵡與鵪鶉的照片去看媽媽,陪她說話,「這是好事,她從此不用擔心叫我而睡不著,也許,我真的是放過她了。」
他真是放過媽媽了,隔週,我們去他家,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:門口一個大紙箱擺滿廢棄的雨傘3、40把,推開門,一屋子舊報紙錄影帶雜物,堆疊到與人及肩的高度,中間窄窄的過道,地上葵花子殼和鳥糞。房間悶而燠熱,不透氣。3房2廳,只有鸚鵡與鵪鶉的房間有冷氣,因怕我們嚇到小鳥們,不許我們進去。書房和臥房,一樣堆滿報紙和文件,他在書本與報紙之間的峽谷打地鋪,睡在一襲紫色的毛巾被,「因為我很濫情。我讀不完的書、讀不完的報紙都不丟掉,累積起來都是大災難了。」
更多鏡週刊報導
【一鏡到底】我是一片雲 李幼鸚鵡鵪鶉專訪之一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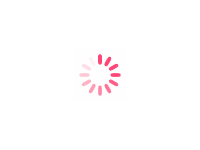


讀者迴響